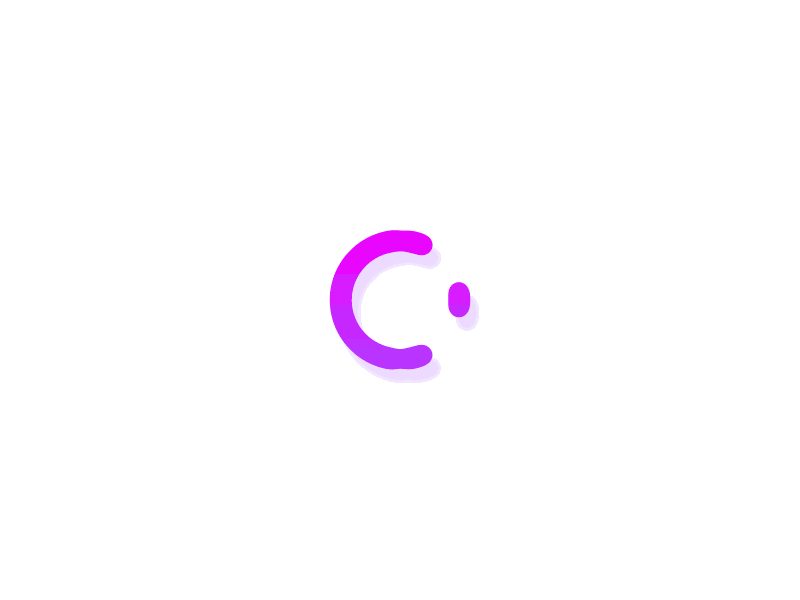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虽然如此,乔唯一还是盯着他的手臂看了一会儿,随后道:大不了我明天一早再来看你嘛。我明天请假,陪着你做手术,好不好? 又在专属于她的小床上躺了一会儿,他才起身,拉开门喊了一声:唯一? 容隽听了,哼了一声,道:那我就是怨妇,怎么了?你这么无情无义,我还不能怨了是吗? 乔唯一闻到酒味,微微皱了皱眉,摘下耳机道:你喝酒了? 容隽很郁闷地回到了自己那张床上,拉过被子气鼓鼓地盖住自己。 如此几次之后,容隽知道了,她就是故意的! 从熄灯后他那边就窸窸窣窣动静不断,乔唯一始终用被子紧紧地裹着自己,双眸紧闭一动不动,仿佛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。 几分钟后,卫生间的门打开,容隽黑着一张脸从里面走出来,面色不善地盯着容恒。 做早餐这种事情我也不会,帮不上忙啊。容隽说,有这时间,我还不如多在我老婆的床上躺一躺呢—— 而屋子里,乔唯一的二叔和二婶对视一眼,三叔和三婶则已经毫不避忌地交头接耳起来。